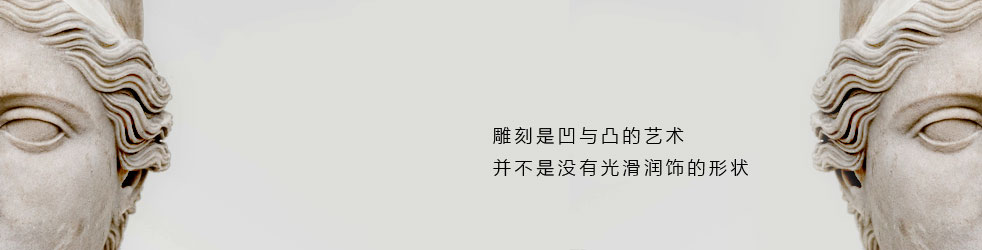
采访是在一种融洽探讨、交流的气氛中进行的。
对“你是从什么时候对人物雕塑感兴趣”的问题,吴教授回顾说,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,在十多年时间内,我完成了大约200多尊中外杰出人物雕塑,主要是中国文化名人,从孔夫子到杨振宁,跨越2500年。当然,更多的是近现代的文化名人。我认为,一个民族要振兴、发展,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科技、经济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之魂。这是支撑一个国家、民族强盛、持久与否的脊梁。
改革开放以来,部分年轻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偶像转向了一些歌星、球星、大款……,这种倾向很自然地忽视了中国传统精华的东西,我以为这对民族进步是一种潜在的危机。作为一个雕塑家,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,用民族精英、人类精英去唤起年轻一代的精神回归。今年5月20日,刚好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,作为一所著名高校,南大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,在一个世纪里,这里曾汇集了一大批科学家、艺术家、哲学家。他们不仅属于南京大学,更属于我们这个祖国,属于世界。我试图用我的雕塑作品去留住哲学家的思考,留住科学家的思维,教育家的思想,用民族之魂去成就民族复兴,以表达我对南京大学这所百年学府的敬意。沧桑历往而又生生不息,南大有一种精神,有一种内在的力量,而这,是通过一大批杰出的人去体现的。南大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群雕,可以形象生动地体现这种精神。
当被问及是如何通过雕塑去体现反映一个人的风格及其内心世界时,吴教授说,可以先从宏观上讲一下。一般讲,塑的文化名人是两类,一类是人文学者,一类是科学家,每一个人的生长都与时代紧密相连,比如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,上个世纪初的康、梁,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等,他们都有着各自典型的时代特征。
塑人是不能不讲长相的,决定一个人长相的有三个因素:一是父母遗传,二是生长环境(自然环境),三是人文环境(个人修养、文化环境,一个人的学养与内涵)。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讲,北方人与南方人不同,有一个名人曾讲过这样一句话,40岁之前不好看怪爹妈,可40岁以后不好看,就是你自己修炼不够。你若仔细去观察一些大家,特别是那些文化人,在达到人生的高境界后,大师与大师之间会出现一种奇怪的趋同现象。因此,在我塑人的过程中,先去找“同”的东西,然后再去找他们的个性。
人文与科学不同。人文深受文化的滋润,人越老就越清癯,风骨凛然,风情万种。那是一种诗的境界,从想象中的老子、苏东坡,到齐白石、冯友兰,都有这样一种感觉,给人诗一般的骨韵,我塑的那件青铜的《诗的沉醉——行吟中的林散之》就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——文化波澜与天地正气的交合……人文学者的思维是跳跃式的、形象的,如李白、李贺等,杜甫有一句“篇终接混茫”就是这个意思。而科学工作者、科学家,他们追求事物发展的真理。在他们那里,方程的解往往只有一个,且大多是定量的。科技是线性的,绝对的,而人文是发散的、相对的。科学家与文化人不一样,数理逻辑与潇洒出尘,可谓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类不同的风范。
世界著名雕塑家熊秉明先生是冯友兰的学生,他看了冯友兰的塑像后对吴为山说,“看了你的冯友兰雕塑,我相信没有哪个人再去做了,因为那里面有历史,有哲学,是一座化石。冯友兰是我的老师,印在我的脑子里,但我做不出来。”正是由于这一点,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才题就了那句“感谢你(吴为山)用艺术留住了哲学家的灵魂。”这不仅使我想起了李白到黄鹤楼看到崔灏在墙上的诗说的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灏题词在上头”那句话。
吴为山说,我塑南大历史上的名人,力求把他们与南大的传统融合在一起。
在塑南大名誉教授杨振宁时,熊秉明先生建议吴为山“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做进去!
怎样用泥去体现数理呢?吴为山说,对杨振宁,心仪已久。1997年认识杨振宁,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,一直有书信往来,1999年在南京大学两人有了一次长谈、对话。吴为山认为,杨振宁是东西文化对立、相融的产物。杨早年读四书五经,对中国的诗、哲学已形成了成熟的观点。不管到什么时候,这种“根”的影响是蒂固的。后来到了美国,他不仅探求科学真理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,以致于从他的形象上,都可以找到这种印痕。他的下颌呈一种几何状,客观、本然、大方,他的头发,一丝不苟,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严谨、理性,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那位数学家的父亲杨武之的“赐予”。
而杨振宁的微笑、一双永远瞪大的眼睛、一双天真的酒窝,实实在在地具备了一个追求真理、追求人文最高理想境界的文化人、科学家的最单纯的品质。他经常吟诵唐代大诗人高适的“性灵出万象,风骨超常伦”,这正是杨振宁自我精神的写照。吴为山告诉我,为了更好地体现杨振宁,特意选用汉白玉,用简练和概括,趋于几何体来概括他,使其灵魂与思想由内而外自然发散。
吴为山回忆到,当时做泥塑时,杨振宁在旁边2个多小时,我汗流浃背,杨先生一会儿微笑,一会儿严肃,一会儿沉思,他甚至说:“你可以摸我的头,你可以感受。”他很懂得艺术家的心,也希望我能表现他纯真的一面。等泥塑样子出来后,杨振宁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,像是在发现科学真理。他让熊秉明看,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。他说:“秉明虽是我的老友,但是哲学家、雕塑家,他可以从远处看我。我弟弟是近距离的,从生活这方面更了解我。”当吴为山完成这件汉白玉作品后,便寄信给杨振宁:“……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,你用自己的人品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……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‘杨振宁’三个字,不要任何后缀(头衔),且最好你自己来写。”出乎吴为山意料的是杨先生在回信中说:“我建议:由你写……”
谈到另一尊雕塑陶行知,吴为山说,陶行知逝世后,宋庆龄为陶行知题写了“万世师表”。因此,我在塑陶行知时,第一个问题就是“师”在哪里?
陶行知讲过一句话,“为一大事来,做一大事去。”它反映了陶行知的人生价值取向及生死观。在雕塑过程中,吴为山说,抛却所有技术,让他与石头融为一体,你看那高度近视的眼睛,中装、平头。一代教育家堂堂正正的师表,须用平实的手法表现出来。
谈到徐悲鸿像,吴为山说,中央大学在艺术教育史上曾经群星璀璨,徐悲鸿无疑是一颗巨星,同时是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大师。以前我曾两次塑过,那么这一次我应该怎样去定位呢?
把徐悲鸿放到他在中大执教时的三、四十年代的旧中国,神州风雨飘摇,而当时的徐悲鸿以一种革故鼎新的精神,融合东西方文化,创造出中国的徐悲鸿。这种创新精神与南大的校风是一致的,这种精神与今天的与时俱进是一致的。正是基于这一点,吴为山在刻划徐悲鸿时,浓浓的头发一分为二,像马鬃一样奔腾、飘逸。而这尊像又是放在浦口校区的一座小山上,远远望去,似风吹来,不屈不挠。从那微微浮肿的眼睛中,透出忧国忧民的神情,高耸、挺直的鼻梁,清楚地彰显了徐悲鸿“独持己见,一意孤行”的追求、执着。徐悲鸿雕像屹立在山巅,那阅尽人间沧桑的沉重,一马当先的姿态,既是艺术的精魂,又是校园的师魂,鼓舞着一代代学子踏实向前不回头。
吴为山还谈到了李四光、竺可桢两位科学巨擘的雕像,在选材上是特意用红花岗岩,放在校园的灌木丛里,太阳升起,不管从哪个角度,都能把斑斑点点的影子印在雕像上,给人一种点点闪闪的烛光的感觉。李四光手拿一个望远镜,神情专注,这是所有雕像中唯一一个用动作表现人物内在气质的。
吴健雄,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女性,后来成为世界核物理女皇。吴为山刻划的是一位科学的母亲,智慧的女神,优雅、宁静、睿智,美与科学、母性的温蕴与追求的坚毅,完美地融于一体。
匡亚明像则表现了一位忠实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老教育家,他的刚劲、他的儒气刻划得淋漓尽致,恰如匡夫人丁莹如教授写的“妙手留容,风骨再现!”
而顾毓琇像则是反映了一位多年侨居海外的百岁老人的赤子情怀:“我不笑,也不哭,我想哭,哭不出来!”这是吴为山教授专程到美国顾毓琇家去做塑像时,顾老先生当着吴教授面讲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。
采访结束时,吴为山教授说,二十几尊塑像安放在校园内,对今日大学生来说,既是文化传授,也是传统教育,年轻人应该从他们身上读懂做学问,读懂做人,读懂一所百年大学的校魂……
发表评论
请登录